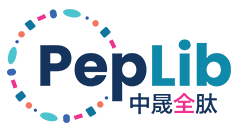动物种属差异对药物开发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25-11-11
作者:
李福燕,中晟全肽研发战略部研究员
引言
新药开发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的系统工程,临床转化失败率居高不下,其中一个关键瓶颈在于临床前研究结果无法有效外推至人体临床试验。在临床前研究阶段,主要是通过体外实验和动物模型评估候选药物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为进入人体临床试验提供决策依据。而作为临床前研究核心的动物模型,尤其是啮齿类动物,与人类在生理学、代谢机制和药物靶点生物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下简称动物种属差异性)。因此,大量候选药物在动物体内的药理和毒理作用不能准确地转化到临床试验阶段,最终因非预期的毒性或疗效不及预期,导致临床试验失败。本文将从动物种属差异的概念及重要性出发,深入剖析在生理功能、药物与靶点生物特性和药物代谢动力学等层面的彼此存在的差异对药物开发的影响,并结合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探讨如何更精准地应对动物种属差异造成的影响,以期为提高药物研发的成功率提供理论依据和前瞻性思考。
一、动物种属差异性的概念及重要性
动物种属差异本质上是指不同动物物种(包括人与动物之间)在生理结构、分子特征(如受体/表位序列)、代谢机制、免疫功能等方面的固有差异。从进化生物学视角来看,种属差异是生物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不同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反映在生理生化层面则表现为代谢途径的定向分化与功能优化、受体结构的变异以及免疫应答模式的分化。例如,啮齿类动物为应对频繁的环境应激,进化出了高效的肝脏代谢系统,其肝脏药物代谢酶的催化效率远高于人类[1];而人类则在长期的社会性进化中形成了更复杂的免疫调节网络,小鼠的免疫系统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人类对复杂病原体的反应[2]。
在药物开发过程中常因动物种属差异而导致药物在生物活性、药理效应、毒性反应、药代动力学特征等方面呈现出物种特异性差异,使得动物模型往往无法准确预测药物在人体内的行为和效果。有多个研究报告指出,超过80%甚至90%的候选药物最终无法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尤其是在心血管和肿瘤等领域,失败率可高达95%。据统计,这些失败案例中有40%至50%是由于疗效不佳造成的,另有30%是由于难以控制的毒性所致,还有10%至15%是由于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性不佳造成的。由此可知,尽管药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疗效不足或安全性问题导致的失败占了绝大多数,而这些问题往往可以追溯到临床前模型与人类之间的种属差异[3-5]。例如TGN1412药物是一种CD28特异性超激动剂单克隆抗体,被开发用于免疫治疗以调节免疫系统平衡。在啮齿动物模型中,其同源物能刺激抗炎细胞因子释放、扩增调节性T细胞,对炎症性自身免疫病有治疗效果。该药物在食蟹猴的临床前安全性测试中,即使剂量高达50mg・kg-1・week-1仍耐受性良好,未出现毒性或全身性免疫刺激迹象。但在2006年伦敦开展的I期临床试验中,6名健康志愿者输注该药物1小时后均出现致命的 “细胞因子风暴”,12-16小时内病情危重。最后经研究发现TGN1412引发的 “细胞因子风暴” 源于其激活了人CD4+效应记忆T细胞。而临床前实验所用的食蟹猴、恒河猴的CD4⁺效应记忆T细胞缺乏CD28表达,导致TGN1412无法在这些动物体内诱导类似的强促炎反应,从而未能预测出人体中的风险[6]。
因此,深入了解动物种属差异对药物开发的具体影响,在临床前实验过程中加以预防,或将有利于提高药物的开发成功率。
二、动物种属差异对药物开发的具体影响
动物种属之间的固有差异具有多层次、跨系统的特征,主要从生理功能、药物与靶点相互作用、药物代谢动力学、遗传与表观遗传、病理模型相关性、应激反应与神经内分泌及免疫毒理与过敏反应等多个层面影响药物开发,这些层面的影响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临床前研究向人体转化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介绍动物种属差异在生理功能、药物靶点相互作用和药物代谢动力学三个核心层面对药物开发的具体影响,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阐述。
(1) 生理功能层面
在生理功能层面,不同物种的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等解剖结构与生理调控机制的差异,直接影响药物的吸收效率、靶向组织分布及机体对药物的应答模式,导致同一药物在不同动物模型中的药效学方面的数据表现出显著差异。
以消化系统为例,有研究发现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生理方面的差异如下:人类空腹胃pH1.5-3.5,餐后先因食物缓冲升高后回落,狗空腹胃pH较高且刺激后胃酸分泌远超人类,兔子胃整体pH低;人类胆汁以胆酸为主且有胆囊(进食调控分泌),狗胆汁盐浓度和分泌率高,大鼠无胆囊且胆汁持续分泌;人类上消化道菌群稀少、β-葡萄糖醛酸苷酶活性最低,小鼠该酶活性高;人类总胃肠道转运时间20-30小时(小肠3-4小时,近端快于远端),比格犬仅6-8小时,兔子转运最慢[7]。这些生理差异将导致药物的吸收在人类和动物中有不同的表现,在开发口服药物时尤其需要注意。在药物开发过程中常用大鼠、狗等动物的药物摄取实验估算人类口服生物利用度,其中就包括2013年美国市场畅销的重磅炸弹药物阿立哌唑(抗精神病药和抗抑郁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销售额达62.94亿美元)和埃索美拉唑(治疗十二指肠溃疡、侵蚀性食管炎等疾病,销售额59.75亿美元)。实验数据表明,这两种化合物在动物体内的口服生物利用度数值不佳。按照当时普遍遵循的“动物数据优先”的筛选逻辑,这类生物利用度低的化合物通常会被认为在人体内也难以有效吸收,从而可能被终止研发。然而尽管动物数据不理想,但研发公司(分别为大冢制药和阿斯利康)可能基于药物本身其它的优势(如良好的疗效、优秀的药代动力学数据等)及对动物种属在消化系统差异性的充分考量,还是继续推进该药物的人体实验。而最终的人体临床试验数据显示,阿立哌唑和埃索美拉唑均在人体内具有足够的生物利用度和显著的疗效,最终成功上市[8]。
因此,以上证据表明,动物种属在生理层面上的差异性在新药开发过程中需要被充分考虑,不能完全依赖该数据对药物的进行评估决策。同时,在药物开发过程中,还需要依据动物种属的不同生理特性进行动物模型的选择,如需要开发治疗胆管癌相关的药物时,不能选择无胆囊的大鼠作为临床前研究的动物模型;而猪模型则凭借其与人类皮肤在解剖、生理、免疫及伤口愈合机制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皮肤病学研究,特别是转化医学研究中最为理想和可靠的大型动物模型之一。
(2) 药物与靶点相互作用层面
动物与人体在药物与靶点的相互作用上涉及许多方面,机制复杂。尽管我们在新药靶点筛选和确认时,会将人源与实验动物的靶点蛋白序列进行比对, 鉴别分子特征(如受体/表位序列),做出初步适用性判断,但这个蛋白序列对比只是种属差异的一个小的方面。还包括空间构象差异及表达调控机制的分化,这些会改变药物与靶点的结合亲和力、特异性,这种种属差异进而会引发药理活性的特异性差异,甚至导致部分药物在动物模型中有效而在人体中失效。以下将从上市药物的著名靶点情况进行剖析,如PD-1、HER2等。
PD-1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的核心靶点,其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成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研究数据显示,人源与小鼠的PD-1蛋白在氨基酸序列上同源性较低,仅约60%,即便是在负责与配体结合、相对保守的IgV结构域,其同源性也只有约75%[9]。这些序列差异导致了二者在三维结构上的不同,人源PD-1的结构相对“灵活”,并且其拓扑结构与典型的IgSF V-set结构域不同,缺少了小鼠PD-1中所具有的C'链,特别是在配体结合区域的氨基酸大小、极性和电荷的差异。这使得PD-1与配体PD-L1相互作用的结合亲和力在人源(hPD-1)与小鼠(mPD-L1)上出现显著差异,hPD-1/hPD-L1的结合亲和力为8.2μM,而mPD-1/mPD-L1则只有26.8μM(见图1)[10]。其中在著名的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的开发过程中就出现了此现象,Keytruda对人源PD-1具有纳摩尔级别的高亲和力,但在小鼠PD-1上,其结合亲和力极低。经研究发现,是因为人源PD-1的第85位天冬氨酸(Asp, D)在小鼠PD-1中被替换成了甘氨酸(Gly, G),当在人源PD-1上进行D85G点突变时,帕博利珠单抗便无法与其结合,这也直接促进PD-1人源化小鼠模型的开发及广泛应用[11]。

图1. 人与小鼠的PD-1/PD-L1结合亲和力
HER2是实体瘤治疗中的明星靶点,属于受体酪氨酸激酶 (RTK) 家族,不同物种间(如人类、小鼠、犬)的HER2蛋白序列同源性为80%-99% [12],同源性高,但是HER2在人类和小鼠等动物中的表达和功能有所不同。如以HER2为靶点的著名上市单抗药物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为例,其在临床试验中发现的心脏副作用(如心功能障碍)在动物模型中却未被预测到,目前未找到具体原因,但有研究表明其核心原因可能是与人类心脏相比,实验动物(尤其是小鼠)心肌细胞HER2 的表达量较低,甚至在某些品系中几乎检测不到,这使得即使抗体能够结合靶标,也难以产生足以影响心肌存活信号的抑制效应[13]。
综上所述,在开发新靶点药物时,不仅要考虑该靶点在人与其它物种的同源性,还要了解其在不同种属间存在的表达差异性,从而更好预测动物模型及临床可能会出现的毒性反应。
(3) 药物代谢动力学层面
在药物代谢动力学层面,肝脏代谢酶系的组成差异、排泄途径的种属偏好性选择,直接主导药物的代谢速率、代谢产物谱构成以及体内蓄积程度,这不仅对药物的作用时长与药效强度产生关键影响,更可能导致动物毒理学评价结果难以有效外推至人体,且将显著提升临床试验阶段的安全性风险。
以肝脏代谢酶系的组成差异为例,肝脏是药物代谢的核心器官,其中以细胞色素P450(CYP450)超家族为代表的代谢酶系参与了超过90%临床常用药物的代谢清除,这些酶系的表达和功能在物种间存在巨大差异[14]。不过相较于CYP450,由醛氧化酶(AO)的种属差异引发的失败案例提供了更为清晰和震撼的教训:SGX523是一款高选择性的c-MET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曾被寄予厚望用于治疗多种实体瘤,然而,在进入I期临床试验后,发现接受SGX523治疗的患者中出现了预料之外的严重肾功能损害,其特征是肾小管中出现结晶沉积物,导致急性肾损伤,这一严重的安全性问题直接导致了该药物的临床开发被永久终止[15]。有研究发现,SGX523的分子结构中的含氮杂环使其在人体和猴体内主要经AO代谢生成低溶解度代谢物 M11,该代谢物通过肾脏排泄时易析出结晶,引发结晶性肾病;而传统毒理学模型(大鼠、犬)缺乏有效AO活性,无法生成 M11,因此这也导致临床前研究未发现肾毒性风险[16]。
综上,一个在标准动物模型中看似安全的分子,可能因人类特有的代谢途径而转化为致命的毒物,因此在新药研发的早期阶段,必须进行超越传统的动物毒理学评价框架。
三、挑战与机遇
传统生物医药临床前药物研发主要依赖动物模型,但是任何动物模型,无论其在基因或生理上与人类多么相似,都无法完全复制人体的复杂性。不同物种间固有的生物学差异,使得从动物实验数据到人体临床结果的外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面对这些挑战,药物研发界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策略,从优化传统方法到拥抱前沿科技,旨在更准确地预测药物在人体内的表现。
(1) 优化动物模型选择与设计
在项目立项初期筛选靶点时,应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析,比较候选动物与人类在药物靶点和关键代谢酶上的同源性,选择最相似的物种。目前普遍的行业共识是,当人鼠蛋白序列同源性低于80%时,应进行交叉反应性的评估;当同源性低于70%时,野生型小鼠模型的相关性大打折扣;而当同源性降至60-65%水平时(如PD-1),人源化模型则被视为进行体内药效研究的唯一可行选择[17]。表1是基于上市抗体、ADC和RDC药物中比较火热的靶点在人与小鼠、大鼠同源性的数据汇总情况,上市ADC和RDC比较火热靶点的同源性均在78%以上,抗体比较火热的靶点PD-1的同源性只有约60%,据资料显示,在开发PD-1相关的抗体药物时常会使用人源化小鼠模型。然而,最终的决策依据是功能性交叉反应的有无,而非单纯的序列同源性百分比,所以还需在后续实验过程中验证靶点在不同种属中的功能交叉反应情况。
表1. 上市抗体、ADC和RDC药物中较火热靶点在人与小鼠、大鼠间的同源性

通常可以使用多种属模型进行验证,其中法规要求使用一种啮齿类(如大鼠)和一种非啮齿类(如犬或猴)动物进行毒理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物种的数据,可以更全面地评估潜在风险。在某些领域(如心血管系统、代谢性疾病),猪、犬或非人灵长类(NHP)等大型动物由于其生理结构和功能更接近人类,能够提供更具预测价值的数据。再者,可以使用人源化的动物模型,即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将人的特定基因(如代谢酶基因、靶点基因)导入小鼠等动物体内,构建“人源化”动物模型。这些模型在评估特定药物的代谢和药效方面,比普通动物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性。如在hPD-1敲入小鼠中,发现帕博利珠单抗在hPD1敲入小鼠中可显著延长中位生存期(MC38 模型40.2天、GL261 模型50.0天)并抑制肿瘤生长,且该小鼠肿瘤和脾脏组织中CD4+、CD8+T细胞均表达hPD1,免疫表型与人体一致,而传统C57BL/6小鼠因无对应靶点表达无法响应人源PD-1抗体,最终证实hPD-1敲入小鼠比传统模型更适合预测人源PD-1抑制剂的药效[18]。值得注意的时,“人源化”动物模型的费用会比普通的动物模型高。
(2) 跨物种数据外推与剂量调整
从动物数据中预测人体有效剂量和安全剂量是临床前研究的核心任务,现有方法一般是基于体表面积或体重,通过数学公式将动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如清除率、分布容积)外推至人体,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校正因体型大小带来的差异,但对于那些主要通过主动转运或广泛代谢的药物,其预测准确性有限[19]。因此,可以运用新的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PBPK)进行计算,这是一种更复杂的计算机模拟方法。它将生物体划分为多个生理相关的房室(器官),结合药物的理化性质和物种特异性的生理参数,模拟药物在体内的完整动态过程。PBPK模型能够整合体外数据和动物体内数据,更精确地进行跨物种外推和首次人体剂量预测[20]。目前PBPK模型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权威机构纳入药物相互作用、特殊人群用药等相关指南,明确其在新药申报中的支持价值,并且由PBPK模型获得的结果可作为临床决策和标签撰写的依据,提升研发过程的合规性和数据可信度。
(3) “3R”原则与前沿科技
“3R”原则(替代Replacement, 减少Reduction, 优化Refinement)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需要平衡动物福利与科学目标,通过替代、减少和优化,实现动物实验的伦理化和人道化,也推动了非动物替代技术的蓬勃发展,这些技术从根本上绕开了种属差异问题[21]。同时,美国于2022年底通过的《FDA现代化法案2.0》(FDA Modernization Act 2.0)显示,允许用更贴近人类生理的替代方法做临床前测试,不用只依赖动物模型。这些新方法包括使用人体细胞改造来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模拟人体组织功能的类器官和器官芯片,还有用算法预测药物效果、设计虚拟临床试验的AI技术,这进一步说明监管机构的重点在于数据的科学质量,而非固守某一种特定的模型类型[22]。
四、总结
综上所述,动物种属差异是新药开发中临床前研究向人体临床试验转化的核心瓶颈,其在生理功能、药物靶点相互作用及药物代谢动力学层面的固有差异,导致大量候选药物因疗效不及预期或安全性风险(如 TGN1412的细胞因子风暴、SGX523的肾毒性)终止研发;而通过筛选高同源性动物模型、应用人源化模型、借助PBPK模型优化跨物种剂量外推,以及结合“3R”原则与类器官、AI等前沿替代技术(契合《FDA 现代化法案 2.0》导向),可有效降低种属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为提升药物研发成功率、增强数据合规性提供科学支撑,推动新药开发更高效地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同时,在确定药物是否要继续推向更高的临床阶段,也不能完全依靠临床前动物模型的数据,还需要进行前期人体实验的验证,充分评估疗效和毒性。
参考资料
[1] Shimada T, Mimura M, Inoue K, Nakamura S, Oda H, Ohmori S, Yamazaki H. Cytochrome P450-dependent drug oxidation activities in liver microsomes of various animal species including rats, guinea pigs, dogs, monkeys, and humans. Arch Toxicol. 1997;71(6):401-8. doi: 10.1007/s002040050403.
[2] Parekh C, Crooks GM. Critical differences in hematopoiesis and lymphoid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s and mice. J Clin Immunol. 2013 May;33(4):711-5. doi: 10.1007/s10875-012-9844-3.
[3] Shanks N, Greek R, Greek J. Are animal models predictive for humans? Philos Ethics Humanit Med. 2009 Jan 15;4:2. doi: 10.1186/1747-5341-4-2.
[4] Balls M, Bailey J. Ethics and Controversies in Animal Subjects Research and Impact on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nesthesiol Clin. 2024 Dec;42(4):593-606. doi: 10.1016/j.anclin.2024.03.003.
[5] Chaulagain B, Gothwal A, Lamptey RNL, Trivedi R, Mahanta AK, Layek B, Singh J. Experimental Models of In Vitro Blood-Brain Barrier for CNS Drug Deliver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t J Mol Sci. 2023 Jan 31;24(3):2710. doi: 10.3390/ijms24032710.
[6] Chaulagain B, Gothwal A, Lamptey RNL, Trivedi R, Mahanta AK, Layek B, Singh J. Experimental Models of In Vitro Blood-Brain Barrier for CNS Drug Deliver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t J Mol Sci. 2023 Jan 31;24(3):2710. doi: 10.3390/ijms24032710.
[7] Kararli TT. Comparison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anatomy,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of humans and commonly used laboratory animals. Biopharm Drug Dispos. 1995 Jul;16(5):351-80. doi: 10.1002/bdd.2510160502.
[8] https://www.pharmainformatic.com/html/blockbuster_drugs.html
[9] Ohaegbulam KC, Assal A, Lazar-Molnar E, Yao Y, Zang X. Human cancer immunotherapy with antibodies to the PD-1 and PD-L1 pathway. Trends Mol Med. 2015 Jan;21(1):24-33. doi: 10.1016/j.molmed.2014.10.009.
[10] Cheng X, Veverka V, Radhakrishnan A, Waters LC, Muskett FW, Morgan SH, Huo J, Yu C, Evans EJ, Leslie AJ, Griffiths M, Stubberfield C, Griffin R, Henry AJ, Jansson A, Ladbury JE, Ikemizu S, Carr MD, Davis SJ.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human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receptor. J Biol Chem. 2013 Apr 26;288(17):11771-85. doi: 10.1074/jbc.M112.448126. Epub 2013 Feb 15.
[11] Picardo SL, Doi J, Hansen AR. Structure and Optimization of Checkpoint Inhibitors. Cancers (Basel). 2019 Dec 21;12(1):38. doi: 10.3390/cancers12010038.
[12] Deng X, Zheng X, Yang H, Moreira JM, Brünner N, Christensen 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volutionarily conserved motif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 predicts novel potential therapeutic epitopes. PLoS One. 2014 Sep 5;9(9):e106448. doi: 10.1371/journal.pone.0106448.
[13]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660379.ch2
[14] Bains RK. African variation at Cytochrome P450 genes: Evolutionary aspect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Evol Med Public Health. 2013 Jan;2013(1):118-34. doi: 10.1093/emph/eot010.
[15] Infante JR, Rugg T, Gordon M, Rooney I, Rosen L, Zeh K, Liu R, Burris HA, Ramanathan RK. Unexpected renal toxicity associated with SGX523, a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 of MET. Invest New Drugs. 2013 Apr;31(2):363-9. doi: 10.1007/s10637-012-9823-9.
[16] Diamond S, Boer J, Maduskuie TP Jr, Falahatpisheh N, Li Y, Yeleswaram S. Species-specific metabolism of SGX523 by aldehyde oxidase and the toxicological implications. Drug Metab Dispos. 2010 Aug;38(8):1277-85. doi: 10.1124/dmd.110.032375.
[17] Brehm MA, Shultz LD, Luban J, Greiner DL. Overcoming current limitations in humanized mouse research. J Infect Dis. 2013 Nov;208 Suppl 2(Suppl 2):S125-30. doi: 10.1093/infdis/jit319.
[18]https://cdn.prod.website-files.com/655dd3c88278aa64954052d4/667d3546d1bf94d6675d1d82_criver-poster-aacr2019-pd-1.pdf
[19] Sharma V, McNeill JH. To scale or not to scale: the principles of dose extrapolation. Br J Pharmacol. 2009 Jul;157(6):907-21. doi: 10.1111/j.1476-5381.2009.00267.x.
[20] Jones H, Rowland-Yeo K. Basic concepts in 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kinetic modeling in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CPT Pharmacometrics Syst Pharmacol. 2013 Aug 14;2(8):e63. doi: 10.1038/psp.2013.41.
[21] Verderio P, Lecchi M, Ciniselli CM, Shishmani B, Apolone G, Manenti G. 3Rs Principle and Legislative Decrees to Achieve High Standard of Animal Research. Animals (Basel). 2023 Jan 13;13(2):277. doi: 10.3390/ani13020277.
[22] Verderio P, Lecchi M, Ciniselli CM, Shishmani B, Apolone G, Manenti G. 3Rs Principle and Legislative Decrees to Achieve High Standard of Animal Research. Animals (Basel). 2023 Jan 13;13(2):277. doi: 10.3390/ani13020277.